互联网时代的文化传承 ——基于非遗社会实践与现象的观察思考
国家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不断实施新政策、新方案,尤其是文化部自2015年开展的非遗传承人群培训计划,成为近几年非遗传承工作的重要举措。非遗传承与保护实践工作的推进,让我们思考互联网时代的传承该如何由文化自发转向文化自觉。大学非遗、社区非遗、少年非遗、海外非遗等传承的关键词,应当在这个传统与现代不断碰撞的对偶时代引发我们的思考和实践。
从万维网诞生到今天的自媒体时代,不论城市还是乡村,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国家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文明转型。现代化、城市化以及互联网带来的全球化,都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的乡村生活。与互联网同时步入我们生活的还有文化遗产时代的到来,随着中国的非遗项目在世界非遗名录中的逐年增添,国家的一系列保护政策相继实施。虽然“非遗”已进入人们视线,但是,传统村庄的减少、农耕方式的替代让非遗原生环境发生改变,自发性的民俗生活在发生流变、衰退甚至消亡,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非遗现象与非遗传承难题,传统与现代的对抗让我们思考今天该如何面对非遗的传承与实践。
一、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生态
在近十几年的时间中,我们迎来了文化遗产时代,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人们的眼光都在逐渐向非遗聚焦,关于非遗的保护方案和措施不断出现。但是非遗消失的速度远快于我们保护的速度,根本原因是非遗所依赖的传统农耕环境的变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1年的51.27%,与之而来的是乡村数量的急剧下降,我国的基层行政村数量从改革开放时的690388个,减少到2011年的589874个,平均每年减少2956个。[1]行政村递减速度尚且如此,自然村数量减少速度可想而知,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时间里,约有90万个古村落消失[2]。
自然村庄的消失意味着村落中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即便是幸存下来的自然村,人们的生活方式相对农耕社会时期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公路、电缆、网络让村落联通全球,传统文化在悄无声息地变化。

安塞的妇女在文化馆传习剪纸,她们依靠便捷的互联网将自己的剪纸作品销售到大洋彼岸。(摄影 苏欢)
1、互联网时代的文化遗产历程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昆曲列入其中,中国成为首次被列入世界非遗名录的19个国家之一。昆曲进入世界非遗名录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在我国正式登场。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4年,我国成为率先加入该条约的公约国。同年,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唐卡、年画、剪纸、古村落、口头文学等一系列文化遗产的建档与整理工作在全国铺开。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正式下发,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十六字非遗保护指导方针,并要求建立国家级和省、市、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同时,各级非遗工作部门相继建立,开启了我国的“非遗四级保护体系”。2006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实施,对国家级非遗的记录、保护、传承,传承人的认定、职责、培养以及各级管理部门的职责等一些列具体行为和要求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一办法的实施为明确我国的非遗四级保护体制工作方法指明了方向,非遗保护开始走向常态化。
以法律的形式保护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赋予缔约国的重要职责。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简称《非遗法》)通过并实施。这部法建立在我国对非遗保护工作进行探索的基础之上,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而制定。《非遗法》的出台将非遗保护工作正式纳入到国家法律体系,使非遗保护具有了法律效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3]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成为热词,使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技艺和精神内涵成为一种价值观,再次引起社会对非遗的关注热潮,杰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频繁登上代表“工匠精神”的人物榜。
在相关文件颁布和实施后,我国自上而下开展了一系列非遗保护工作。2006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国务院分别公布了我国第一至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共计1219项,期间另有省级非遗名录8786项,地市级非遗名录18186项,县级非遗名录53776项[4],共计8万余项,同时伴随着代表性传承人的评选和相关活动的开展。
以上数字让我们看到我国巨大的非遗资源,也代表着各级管理部门在非遗保护方面做出的切实努力。文化遗产时代已经到来,非遗保护工作已经走上日常化轨道。自上而下的非遗管理工作让我们看到了非遗保护的成效,但是,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问题也越发突出,如专项资金短缺、非遗传人评选制度疏漏等。

中央美院第四届中青年非遗传承人群研培成果展在太庙举行,这是文化部与大学对非遗传承进行的联合探索与实践。
2、互联网时代的乡村生活变化
90年代初万维网在美国诞生,随即传播到世界各国,也来到了中国。互联网这张无形的大网让世界上任意两个点在任意时间交汇,它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也改变了非遗依存的乡村生活。网络刚诞生之际,全球的互联网用户为20万,20年后,全球拥有30亿网络人口。巨大的信息充斥在我们身边,互联网无时无刻不在惠及和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也为改善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销售方式带来了福音。
90年代初,我国对农村地区实施了“村村通”[5]工程,在实现了绝大多数的公路、电力、自来水、电话网络的通畅后,“村村通网络资讯”工程发起,这项工程要让每一个村庄接通网络,让农民像市民一样获得便捷丰富的咨询。截止至2006年,我国97.6%的村庄安装了电话,57.4%的村子安装了有线电视或网络。[6]截至2015年12月,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7%,中国农村网民数量达1.95亿,占我国全体网民的26.9%。摩托罗拉、华为等手机制造商专门在农村地区推出160-800元的低价手机,手机上网成为带动农村地区网民增长的主要动力。[7]
乡村中使用网络的大部分是接受过基础教育、会操作电脑的年轻人。年轻传承人的信息生活和城市无异,传承人将自己的作品上传到网络平台,作品面对的是30亿网民受众,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宽广的领域。年轻的传承人通过一部手机结识热爱非遗的海外客户,并把作品卖到国外,更有很多年轻人用便利的网络开起淘宝商店,销售作品。
除了销售作品和自我宣传,网络也是传承人获取非遗咨询、接收上级通知的主要方式。网络的繁荣对非遗传承也暴露出一些实际问题。例如,在网络普及的情况下,六十岁以上不会使用互联网的老一辈传承人逐渐脱离活跃的传承场域,信息的不对等封闭了老一辈的传承时空,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的传承发展。

云南孟连一座佛寺的开光仪式间隙,来自布朗族村寨的年轻女孩正在用互联网沟通世界。(摄影乔晓光)
3、互联网时代的农民移动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带来了改革开放政策,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任务需求大量的劳动力,农民离开土地涌入同一个目的地——城市。农民的移动改变了村落的人口结构,改变了农民延续了千百年的农耕社会生活。
80年代开始的“农民工潮”是我国建国以来继“大跃进”、“上山下乡”后的第三次大规模人口迁徙,这次人口迁徙的数量远大于前两次。大跃进时期人口迁徙数量大约占我国总人口的4.5%,上山下乡时期的人口流动数量约占总人口的2%,[8]而在2005年,农村流动人口数量为1.4亿,[9]占总人口的11%。这一数据在2015年的统计中再次被刷新,此时我国的农民工人口数量为2.7亿,[10]乡村人口数有6亿,也就是说,45%的农民都在城镇谋生。
青年人对城市充满向往,他们是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改变乡村生活方式的重要力量。2004年,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9岁,30岁以内的农民工占到总数的61%。[11]城市中的农民工快速融入新生活、接触新事物,他们用电话、网络与家乡联络,将城市生活快速传递到乡村。影响最直接的是年轻人的定期返乡,他们将城市里的服饰、信息、生活习惯甚至互联网直接带到乡村,让更多的村民认识外面的世界。
城市生活不得不让年轻人长期放弃乡村里的信仰和民俗,只有重要节日或活动回乡时才有机会接触民俗。这些民俗对年轻人来说遥远而陌生,有的年轻人用手机拍摄照片、视频上传到网络,原本的参与者成为游客般的旁观者;也有部分年轻人对“新鲜”的乡村民俗产生兴趣,模仿老人的样子学习、体验传统民俗,可是过不了多久,他们又要投身到忙碌的城市生活中。
年轻村民像候鸟一样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往返,移动数量与乡村生活的变化成正比,巨大数量的农民移动对传统民俗的改变产生巨大影响。农民工将互联网生活带到乡村,让乡村中的农民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形成乡村与城市沟通的循环往复,乡村生活和传统民俗在循环中逐渐弱化。现在的乡村是缺乏年轻活力的乡村,民俗活动的组织只能靠老一辈支撑、维持,非遗的存在环境、生存状态在农民的迁徙中发生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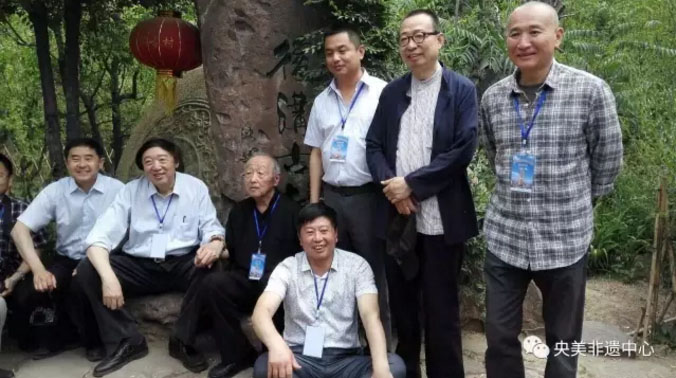
十三年前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项目在山西后沟村启动,农村在缩减,但古村落进行抢救与保护工作在持续。(图中为冯骥才、乌丙安、罗阳、潘鲁生、乔晓光等古村落与非遗保护专家)
二、互联网时代的非遗传承现象
丰富的信息资源改善了农民的生活,为传承人提供了更多机会,有利于非遗普及和宣传。同时,传承人对互联网的接受也改变了非遗的传统形态和传承人的传承状态,一些列文化现象相继产生,这让非遗传承实践面对不同于以往的挑战。
1、文化物流
互联网的最大优势是为人们在任何地点提供无限的信息资源,这一特征产生了非遗时代的“文化物流”现象,即在互联网的影响下,非遗类型、文化符号甚至民俗从源生地流通到另一地区展示、销售或表演。
互联网的普及将各地的非遗资源搬运到传承人眼前,无时无刻不在激发传承人的创作欲望。传承人在创作前期以个人审美倾向选择参考图像,在不顾忌地域的情况下,无意中将外地的非遗“物流”到自己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在传承人新创作的作品中看到各种地区、各种文化的图像来源。当地的传统工艺品中受欢迎的图像有可能正被运输到其他城市,即将出现在另一位异地非遗传承人的作品中。
近几年,博览会成为非遗传承人传承生活和提高经济收入的重要方式,频繁的博览会也是文化物流现象发生的重要源头。传承人通过上级推荐或手机网络在第一时间获得展会或展览信息,之后便带着他们的各式作品奔赴展场,甚至有的传承人带着作品参加海外会展活动。全国各地、各种门类的非遗产品在同一时间集中在同一场所展示,为传承人提供了销售作品的充分契机。

2016年济南非遗博览会上,传承人们汇集一堂展示技艺,同时也销售作品。(摄影张冬萍)
对于参会传承人来说,博览会为大家提供了交流学习的机会,而这种“学习”经常是对图样的借鉴,传承人会相互参考利于销售的品种学习、制作。我们可能会在内丘神码的摊位上发现东南沿海风格的年画,会在西南少数民族剪纸的摊位上发现陕北地区的剪纸花样,甚至外国风格的剪纸也“流通”到了中国传承人的作品当中,地域文化特征被忽略。对于消费者而言,展会为他们提供了极大的购买选择空间,任何地区的非遗都有可能出现在购买者家中。对于具有民俗内涵的作品,消费者并不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甚至不知道名称,博览会上的文化物流让非遗失去地域性的存在含义,成为单纯摆放在家中的工艺品。
2、文化同质
文化物流现象带来的一大结果就是文化同质化问题。互联网、博览会、农民迁徙等事件直接改变了非遗的传承方式,使一些在我国广泛分布的非遗类型出现作品千篇一律的面貌。传统的传承是在祖辈的指导下学习非遗技能,并在乡村生活中自觉积累与非遗相关的民俗文化知识,构成传承人“技艺”和“记忆”的双重知识体系。今天的非遗传承除了师傅传授,网络成为年轻传承人离不开的学习方式。多元化的知识对传承人开阔眼界、丰富知识体系固然有益,但若不加以正确引导,所谓的“学习”就成了不加分辨地“搬运套用”。
尤其对于传统手工艺领域的传承人,绝大多数中青年传承人都有通过在网络上寻找图像资源而获得创作灵感的经历。传承人在作品中“嫁接”网络资源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将其他地域或领域中的非遗图像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两个远隔千里的文化风格经常出现在同一地点;第二种是将风景名胜等图片转化到自己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名胜古迹在不同的技艺中被不断复刻。以上这两种现象直接导致非遗失去地域文化特征。还有一类是将古今中外的著名画作用自己的传承技艺复制,力求逼真,出现模仿学院派的趋势。以上三种非遗创作的新模式造成的共同结果,是让全国各地的非遗面貌出现同质化倾向。长此以往,外来风格被频繁使用,当地传统被弃之弊履,导致当地非遗特征淡化。在2015年“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剪纸交流展示活动中,我们看到全国27个“剪纸文化之乡”的创作中出现了类似的创作主题、相近的语言风格,一些作品几乎无法从图像上区分地域。

成都国际非遗节上,多民族的传承人与国际友人进行交流,也把中国的非遗传播到世界。(摄影乔晓光)
3、文化流变
无论古今,文化流变是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和过去相比,今天的文化流变发生的更突然,变化速度更快,外力因素更突出。互联网信息、农民的移动都在对文化流变产生影响,文化物流引起的文化同质本身就是非遗传承中的流变现象。另外,社会风俗、礼仪、节庆类的非遗变化更为显著,对于已经成功申请非遗的习俗仪式,人们有意识地按照传统模式有序传承,而尚未进入非遗名录的习俗正在被简化。
传承人对非遗的传承情况也在发生流变。传承人对“记忆”的掌握越来越少,单一的“技艺”学习让传承的完整性缺失。例如,传统陕北剪纸的很多纹样是使用在巫俗当中的:“扫天婆”挂在院中求晴免涝,“瓜子娃娃”贴在门上辟邪挡鬼,“碰头娃娃”贴在院子水缸上以祈天降雨……现在人们很少再通过铰娃娃许愿,失去民俗实用价值的剪纸演变为图案纹样出现在剪纸创作中,使制作目的、使用方法、悬挂方式发生根本变化。
很多传承人生长在乡村,现在基本都在县级以上地区生活、工作,即使掌握传统民俗也无法在城市生活中复现。农民从乡村移动到城市,让传人失去学习民俗的基本条件,新一代对非遗产生“文化陌生感”。乡村的民俗、信仰失去年轻一代的传承群体,非遗的原生环境不再,年轻人传承的仅仅是技艺,“重技艺”、“轻记忆”的事实成为非遗传承流变的一大现象。

八十年代将中国剪纸带到法国的剪花娘子李秀芳,现在与子孙三代共同传承剪纸。第一排从左至右依次为:张志学、乔晓光、陈山桥、李秀芳。(摄影 苏欢)
4、文化“新”功利
传统乡村生活中的民间美术或民俗仪式具有实际的民俗功能或信仰功能,通常来说,求子长寿、招财纳福、驱邪禳灾是具有民俗功能的非遗类型稳定不变的“文化功利”主题。我们熟悉的年画、剪纸、面具、银饰、刺绣、建筑彩画等纹样都以此功利目的制作,并在民间信仰、民俗仪式、生活用品三个层面的使用中实现其价值。功利性驱使非遗被使用、传承,是非遗在原生环境中得以传承的根本动力。但是,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科学知识被广泛普及,解决问题的渠道不再单一,即便是生活在乡村中的人们,生活习惯也越来越接近城市,非遗失去了功利性传承动力,继承便成为难题。
进入文化遗产时代,非遗传承人评选成为刺激传承的新动力,这是新时代的“功利性”。一些传承人努力取得更高级别的传承资历,为他们带来更高的荣誉、更多的展览机会、更显赫的名声地位,最终将为他们的作品带来更高的价格,这些和传承人的经济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非遗传承人评选本身为传承非遗而设立,在个别地区这些利益败坏了非遗传承人评选的初衷,非遗传承人成为人们的利益争夺点,制造出一些列传承矛盾,真正技艺优秀的传承人难以上榜,扰乱正常传承秩序。
一些传承人的作品已经脱离开民俗生活,非遗的服务对象发生改变,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传承的文化生态、传承人的传承心理创造新的文化功利,用新的文化功利价值连接传统与当下,促进非遗健康传承。这种功利性在于将非遗回归到日常化的生活当中,是具体而切身的,不能是单纯的经济收益,不能是项目化的利益刺激。
三、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关联着多民族文化的社区生活,非遗的文化传承不能仅仅在体制内进行项目保护,更应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生态中进行可持续探索。文明转型期的非遗传承面对多元化的语境,涉及到大学教育,也涉及到中小学教育,也涉及到高校与社区传人的互动,多方位的探索实践让非遗全面步入互联网时代的传承发展阶段。
1、大学与非遗
2015年,文化部联合教育部组织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全国57所高校展开。大学与非遗或民间文化的互动自20世纪初业已开始,[12]这次培训成为大学教育和社区非遗文化传承发生关联的绝佳契机,让高校再次参与到非遗传承保护的行列,也为高校师生与社区传人的教学相长提供了机会。
在这次培训中,中央美院作为最早开始培训的项目试点院校,为培训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经验。重视民间美术教育是中央美术学院的传统。五十年的中央美院成立了“泥人张”、“面人汤”、“皮影路”工作室;八十年代中央美院成立了民间美术系,邀请陕北“剪花娘子”到学院讲学;进入新世纪,中央美院成立了国内首家非遗研究中心,成为较早开展非遗教育的高校。中央美院在培训过程中结合多年教学和研究经验探索出“三知”、“三化”的培训经验。“三知”即“文化要知情”、“技艺要知艺”、“发展要知辩”,“三化”在“三知”基础之上提出,即“常态化、互动化、职业化”。“三知”让“让传承更加传统”,倡导新时代的非遗要“为民族传承,为生活创新”,“三化”让非遗培训更加贴近社区传承的实际情况,让传承更加靠近非遗的活态本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曼谷召开的“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生学位课程发展区域论坛”,尤其强调大学对区域性非遗保护的作用。培训让大学直接参与到解决基层社区文化遗产传承问题的实战中,再次让高校对社区中的非遗传承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观察与思考。
2、社区非遗
多民族社区非遗的活态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的根基,乡村社区是区域文化发展的精神情感之源,是非遗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传承实践的过程尤其要关注社区群体。中央美院在培训后让大学生进行了“社区回访”,即回到传承人生活的社区考察非遗实况、发现培训问题,回访成为在培训高校普遍推广的成功经验。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在社区中认识非遗、学习非遗,奖技艺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当中;传承人将自己难以实现的创作想法与大学生探讨,合作完成培训结业作品,形成互动互惠的培训模式。此外,中央美术学院在剑川、贵州等少数民族乡村社区设立了实践教学基地,让大学生直接进入社区学习非遗技艺,并在教学基地开展“艺术介入乡村”实践。
社区考察是高校研究非遗、提出传承办法不可绕过的一步,我们有必要在社区中解决社区的问题,在以社区为本的基础之上检验和改善培训经验,探索和发现非遗传承的有效方法。另外,社区非遗的文化认知也是社区传承人群参与实践的核心内容,除了高校对社区非遗关注,还应鼓励社区内的人进行当地的基础田野调查、非遗资料整理,带动非遗的社区传承。

1986年,陕北的剪花婆婆赴央美传习剪纸,至今中央美院仍持续请民间艺人进校园,然而民间天才传承人在逐渐离我们远去。
3、少年非遗
在文化快速流变的今天,对于“文化陌生”的年轻一代,在文化遗产地进行教育传承是不可忽视的传承方式。传统农耕社会时期,非遗传习练就的都是童子功,代代相传的文化是从童年和少年开始的。少年时期是接纳手工技艺与文化启蒙的最佳阶段,我们应探索非遗的地域文化资源与艺术资源,以适合的方式在少年中开展认知实践和启蒙教育。教育部开展的“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工作,将农村学校艺术教育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与优秀民族文化传承相结合,让农村学生享受公平优质艺术教育的同时也促进了地方非遗的少年传承;国家艺教委“成就未来工程”中的“‘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将民间美术资源与美术教育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思考非遗在儿童美术教育中的普及提供了经验方法。
与上世纪相比,古老的文化记忆处在断裂的关口;与上一代传承人相比,青年传承人的文化记忆在逐渐衰减。不同民族社区的许多非遗传统仍在,应利用好民俗、节日,让少年儿童在“技艺”实践环节参与艺术体验,在“记忆”接受环节加深对非遗传承的介入,可将将非遗延续。少年非遗关系着更长久的未来,让少年参与地域性非遗互动,为学校里的少年讲好民族文化的每一课,这是需要全社会来关注的事情。

“蒲公英行动”黔东南校点,邀请民间剪纸艺人走进学校教孩子们学习苗族剪纸。(本图由“蒲公英行动”提供)
4、非遗的海外传播
中国已有40个项目跻身世界级非遗,项目总数位居世界第一,是名副其实的“非遗大国”,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在不断增加,国外对中国非遗的关注度和热情度也越来越高。扩大中国非遗在世界的影响力是互联网时代需要提出的问题。2004年孔子学院建立,十年的时间里,孔子课堂遍布全球 125 个国家和地区;文化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组织的官方或民间海外文化交流活动接连不断。网络将世界的每个点连接起来,中国的非遗也需要打破国内疆界向海外推介、传播。
将非遗进行海外推广应与国内的非遗传承工作相区分,国内非遗传承目的是传承社区内的文化和技艺,而国外非遗推介侧重个体体验和文化认知。非遗的海外传播不能像要求传承人那样掌握非遗的文化和技艺,而是在文化平等、文化尊重、文化包容的背景下,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向海外,用中国的非遗进行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尤其是那些国内外都具有的文化传统,可成为沟通两国的文化媒介。以剪纸为例,剪纸是中国的世界非遗,在中国普遍存在,在日本、美国、德国、希腊、墨西哥等一些国家也存在。剪纸既是外国人熟悉的,又是中国独具特色的,在中国剪纸推向海外的过程中,既能以剪纸作为共有的文化背景,又可将中国剪纸推向世界。在剪纸的世界推广中,中央美术学院十多年不断地与不同国家进行文化遗产主题的剪纸创作合作,以剪纸这种文化遗产的方式与世界对话。这一过程既推动了乡村社区的剪纸活态传承,也推动了世界对中国剪纸艺术的认同与接纳。[13]
结语:创造性传承的时代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和日常化推动了传统文化的复活与再现,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在时间张力上面对新一轮的冲突与融合。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与现代化的对话与对抗相互伴生着走到今天。不同民族时间意义的根性几乎代表了他们最深刻的人性价值观、世界观以及文化信仰的生存观。非遗传承在时间意识的混生中正在酝酿新的时代风尚与文化波澜,客观现实要求我们接纳这个文明的对偶时代,接纳这个变化的时代赋予我们的挑战,用创造性的方法面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类型、不同情况的非遗传承问题。
从不同民族村庄的活态文化中发现一个民间的中国,发现那些我们古老的中国故事,面对传统与现代两种互补共生的时间,创造性传承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选择。





